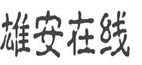柴静正牌心灵鸡汤:人最大的痛苦就是心灵没有归属
文章摘要:柴静正牌心灵鸡汤:人最大的痛苦就是心灵没有归属
人最大的痛苦是什么?如果问你?你会怎么回答?如果问我,我会这么回答,人最大的痛苦就是失去了最亲的人。很多人肯定还会这么回答,打一辈子工都买不一套房子,很痛苦。更有些人会这么回答,辛苦了一辈子,都没有钱去结婚,至今还在单身,也很痛苦。

可以看出每个人认为的痛苦事情都不一样,有的人认为的痛苦事,在别人眼里根本不叫什么痛苦。所以说你认为的痛苦,别人或许不会理解。别人的痛苦,你也不会理解,因为痛苦不一样。即便拥有同样痛苦的人,比如都同时失去最亲的人,但这个痛苦的程度也不一样,从而导致痛苦的人心情也都不一样。
那么说起人生最大的痛苦,我们不妨一起来读一下柴静很精辟的语录,道出了人最大的痛苦,很多人都有,无法逃避!文字如下:

人最大的痛苦就是心灵没有归属,不管你知不知觉,承不承认。——柴静
读完这句语录,让人不得不重新认识这个问题。很多人为什么平时感到很烦人,很烦闷,说白了就是心灵没有归属。记得三毛曾经说过跟这句名言差不多的话,叫心没有栖息的地方,到哪里都是流浪。那么心灵没有归属的人,心里就会总感觉失落落的,没有人生方向。
心灵有归属的人,他知道为这个归属去奋斗
心里装着人的人,一般都是幸福的,哪怕是思念一个人,哪怕是暗恋一个人,哪怕是单相思某个人,都是幸福的。人生最大的不幸福,最痛苦,就是找不到人去喜欢,找不到人去思念。在这个梅雨的季节,找不到人思念,是什么样的感觉,这种感觉就像三毛说的一样,感觉在流浪。
也只有心里装着一个人,有归属,每天就不会想七想八,就会感觉心里充实的舒服。所有的努力和奋斗都会有目标,哪怕只是让那个心里这个人生活过得更幸福,都是一种目标。他更可以为心中归属的人去吃尽世间任何痛苦,可以尝尽人生百态,一切只为了她。
倘若没有她,他就吃不下很多苦,就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,可想心里有个归属是多么重要。我们都希望这个归属是长久的,是一生的,是一辈子的。但有时候老天总喜欢跟自己开玩笑,是一阵子,过了这个阵子,心里的她,就离开了,我们心灵又一阵失落,没有了归属,人生又没有了方向。
心里有归属的人应该好好珍惜这个归属,而不是吃在碗里看在锅里
很多人心里有人了,有了归属,还到处喜欢沾花惹草,这种人是可恨的。这种人往往对感情,也不是专一的。这种人就有张爱玲说的红玫瑰与白玫瑰心里,得不到永远是最好的。得到了红玫瑰,却想着白玫瑰。得到了白玫瑰,却想着红玫瑰。这种人心里虽然有归属,但是很快就变得没有归属了,因为他不珍惜,甚至不真心。
我们要把感情给一个可以依靠一辈子的人,而不是一个花心大萝卜,得到了不珍惜。得到了不珍惜的这种人,是不配拥有心灵的归属的,这种人就应该永远单身,永远痛苦下去。
很多人痛苦是对自己心灵的归属要求太高了,所以很多人即便是结婚了,心灵也是找不到归属。因为他结婚,完全是为了传宗接代这个大任。倘若人生让他重来一次,估计他会晚点结婚,直到找到心灵的归属再结婚为止。
因为没有找到心灵归属就结婚的人,一般婚后婚姻生活是不和谐,是不幸福的,是痛苦的。所以说柴静很精辟的语录,道出了人最大的痛苦,很多人都有,无法逃避!
附:柴静原文
01
我刚做记者的时候,东方时空的制片人时间说过一句话,去现场采访的时候“要象外国人一样去看”。
他的意思是不要熟视无暏。
我以为自己听进去了,看一个美国人写的中国,才知道我对现实已经失去多少感觉。
他写 “任静要出去打工,妈妈有点惊慌失措地追着女儿到了工厂门口,求她留下来,说她太小了,姑娘什么也不说,也不看她母亲,那女人求着情,突然大哭起来,女孩儿依旧不为所动。最后,母亲让步了,大声叫着“去吧,你愿意去就去吧”
她转过身,慢慢穿过马路,大声哭喊着。
她一走开,女孩儿也不自禁大哭起来------把头埋在双膝间,抽泣起来。接下来一个小时,母亲和女儿站在街道的各一边,哭泣 着,她们都很生气,不跟对方说话,不看对方一眼,可母亲还是不愿意离开。
姐姐来了,隔着路给妹妹传口信“她叫你当心”
十六岁的女孩回了一句“告诉她,我不会有事的”
五分钟后,姐姐说“她哭了,她是真想让你留下来”
女孩口气很硬“今天晚上一到那边,我就给她电话”。
工人们装好了车。她终于爬了上去。最后,母亲眼看着所有的哀求都无济于事,就送过来两百块钱。站在那儿看着车消失,泪水从脸上落下来。
另一对姐妹也在这个车上,来送的是父亲,没有拥抱,没有伤感,他关心的是更重要的问题“衣服要暖和,天气凉了,不注意要生病,生病了又得花钱买药,要穿暖和,好吧?”说完这些,转身大步走了。”
中国古老的乡村就在这个细节里挣扎着,又绝不回头地消失了。
02
何伟在90年代来到中国人,生活在小城市,一个美国想在中国默默观看什么事而不成为被注意的焦点,会有多难。但看看他写的清明这天的中国:
“早上杏花落了一地,象春天的暴雪……几个男人在土坟前转‘这儿埋的是我爷爷’
‘才不是呢’
‘我觉得是’
‘瞎说,那是你爸的大哥’
何伟写“他们很少提到人的名字,只提跟某人的关系,也没有相关的细节,没有具体的记忆。”
其中一个坟墓是新的, 是一个前两年刚搬到城里的老头儿,坟上新鲜的泥土堆得很高,何伟拿起一把铲子,给土堆上填了一点土。“有人拿起一沓冥币,点了起来。另一个人拿了一支香烟,插在坟头上,香烟笔直地竖立着,几个人退后一步,看着这土坟,议论两句
“他实际根本没抽过红梅”
“对,贵得很,他原来都抽黑菊花”
“现在买不着了,80年代的时候流行”
这是人们提到的唯一与死者有关的细节。站了一会儿,魏说“好,走吧”
其中一个转头看了看“烟没事吧?”
“没事儿”
他们几个人“顺着那条之字小路,下到了沟谷里,地上是杏花花瓣,高音喇叭里正在播送一年一度禁止上坟烧纸的通知。一行人回到地里干起活儿来”。
这个拎着铁锹的美国人,看到了我熟视无暏的中国。
03
何伟在美国的时候叫彼得海斯勒,他在小学校里讲中国,让小孩子提问,孩子问“中国父母杀掉女婴吗?”“中国人吃狗吗?”,他感觉很糟糕,“怎么两个问题都是这样子的?”
他在中国面临同样的问题,在四川涪陵教书的时候,课本上对于美国宗教的介绍是有什么样的邪教,对于学校的介绍是发生了什么样的凶杀案。他对学生解释“这些事是真的发生的事,但它不能代表真正的美国社会。”
他希望人们描述一个国家要讲清楚那些背景,用时间去长期采访“而不是简单告诉他们什么是最不好和最好的事情”。
04
1996年,从牛津大学毕业,何伟坐火车到处旅行,经过北京,原来打算呆一周,决定留下来因为这里的人“比较活泼”。
27岁他作为志愿者来到四川的小城市,“生活在这样一个小地方你几乎看不到什么外国人,我喜欢这种挑战。我也喜欢长江和那里的风光。涪陵比四川中部更加多山,我喜欢在那里跑步或者远足。”
他没学过中文,不是任何媒体的记者“因为以前没有研究过中国,我对这里的人和物反而没有什么强烈的态度或意见。有时候你缺乏相关知识不是坏事,中国变化太快了,如果我1980年代真学了什么有关中国的东西,到1996年它也早已过时——中国已经变成另一个国家了。”
2001年他申请了驾照在中国漫游,租了一辆北京产的切诺基沿长城行驶,外国人租车是不能离开北京的,不过他已经学会了小小的违规,如果车撞坏了,租车的人会拿出一张“美中拖拉机协会”的空白介绍信算作他的单位。他写下人们对他的各种反应“不管限制是什么,它都是现实的反映。”
他不能在车上带GPS,害怕在西部被当成干测绘勾当的外国人,他在小旅馆住宿有时会被上报给警察局,“罚一点钱”,所以晚上他住在主路分岔出去的土路上,午夜帐篷突然被照得通明,他猛地坐起,以为是驶近的车灯,拉开门帘,才意识到是圆月升上地平线,他在那个月光里“静静地坐着,等待我的恐惧平复下来”。
他沿着长城漫游,后来在怀柔一个偏远的小村子里生活下来,租住在魏家,墙上是《还珠格格》的海报,和一对双胞胎小男孩的大幅画像,“生双胞胎对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,是唯一可以合法拥有两个孩子的方式,其实就连这张像上的双胞胎也不是真正的,只是一张复印了一份,反着放在一起。”茅房里两块石板中间留着小缝算是蹲坑,晚上睡觉他听到老鼠在墙上跑动“每当月圆的时候,这些家伙尤其活跃,在那样的夜晚,我能够听见它们把核桃滚到屋顶的秘密仓库里藏起来”
自从他租住在三岔村后,村子里叫“搅屎棍”的人向警察告发他。他知道“警察只是不想有麻烦”,他找出法律条文,主动去拜访了警察,中秋送了月饼,春节送了水果,终于有一天警察对搅屎棍说“别作无用功了”。
05
看了何伟这本书,很多美国人对他说:“我一直觉得中国到处都是公安。但是看完这本书却发现,并不是这样的。”
这本书的封面上是西部荒凉的公路,路边放着一个塑料片做的警察,这是在中国常见的场景,何伟说他选这张照片的意味是说“在中国很多地方其实是没有权力机构管的,是市场和普通人自己在管”
得普利策奖的华人摄影师刘香成说过他拍中国的方式“我并不刻意去拍政治,我只是拍了普通人的生活,只不过普通人的生活里反映出了政治”。
何伟经常被问,“中国的政治下一步会怎么改变”他说这种问题特别难回答,“实际上对于我来说不是太重要,我在中国的工作不是改变中国,或者改变中国人的想法。我关心的只是今天他们怎么想”只不过,他说,在不到十年的时候里“所有人都改变了对自己的看法,也都改变了自己与周围世界的关系”,每个人都在剧烈地变化,反复摇摆,有时自行其是,有时候被裹胁而去。
他很少对这些人评判,只是了解,但有一个细节除外。
六岁的魏嘉经常感冒,他父亲的反应是把名字改掉。嘉这个字有十四划,不吉利。计算机分析说五行中缺水-----何伟说,“我在中国认识的人基本上都缺水”。计算机给的方案是“淞”。
改完名字之后,孩子总是一言不发,大人问好几遍,他回答“不好”。有什么不好,他不给理由,也没提出另做选择。跟往常不一样的地方是,他没生气也没冲着他妈吼叫,他的反应只是一句“不好”,这两个字还是自言自语说出来的,时间慢慢过去,这种克制态度产生了一种奇怪的结合体,当中有无能为力,也透露些许力量。他爸爸无法明白哪儿“不好”,很快就懊恼不已。
对这孩子来说,电脑已经给他承诺了鸿运当头,大富大贵等等,但到头来,这一切统统“不好”,反正就是拒绝使用。
几个星期后,他的父亲放弃了,再没提起这个名字。
写完这个故事后,何伟不常见地写了一句有点抒发感情的话“从此以后,他永远叫魏嘉”。
对这个并不与什么对抗,只是要成为自己的孩子,何伟好象有某种敬重和感情。
06
前阵子,我爸打电话给我,说家族决定把老房子拆了卖掉。这是一个三百多年的清代宅院,我在那儿出生,长到八岁,一个人关于熟悉和稳定的感觉都从那儿来。我爸问我“你看你什么意见?”
这个房子的产权属于十几户家庭,我也没有那个财力去买那个房子,我只能说“由它去吧”
放下电话,我想,由它去吧,对所有我干预不了的事情,我只能狠狠心,由它去吧。就当是看历史,旁观好了。我早就变化成另一个人了,我不需要这些。别动感情,就这么着吧。
我认为我已经忘了这件事,看何伟的书,我才重新感觉到内心的掀腾。
在他书里,写到这个家庭里,魏嘉的大伯是一个智障聋哑人,村里人叫他傻子,没有人理他,只有不满6岁的孩子跟他玩,玩的时候他很欢乐。何伟每次试图跟他说话,都被村民拦住“他听不懂”。
有一天,魏嘉的爸爸让何伟开车送一家人去镇政府,到了门口,开开门,他把傻子拉下了车“政府应该每个月给我们钱养他的,他们不给,我只能把他留在这儿,直到他们愿意出钱为止” 。傻子没有任何表情。
魏带着他哥哥穿过院子,走过一个金光闪闪的大钢球雕塑,进了大门。
下午稍晚的时候,领导们用车把人送回了大山里,在离村子里还有几公里远的地方停下了,傻子从来没有一个人离家那么远过,但他靠本能找到了回家的路。
何伟再回到三岔村的时候,傻子远远地看见他,咧着嘴大笑,指着轿车,比手势,是在讲述坐过他车下山的事。
“我懂”何伟说“我记得”,他想道个歉,说自己当时明白这事儿的时候,已经太晚了,还是把傻子丢在政府了。但是怎么也找不到一个办法表达歉意,傻子还在那儿激动地大大比划着手势。
后来补助就有了,再后来还给残疾人发了彩电,魏嘉的爸爸把彩电送给了一个“关系”-------“反正傻子也看不懂”。傻子晚上一个人坐在黑屋子里。
等孩子6岁之后,长出了父亲一样的桶状胸脯,也学会了像其他人一样对傻子不理不睬。
何伟写出了我熟视无暏的中国,和那种亲切的酸楚。那个酸楚就是剧变的实质-------人最大的痛苦就是心灵没有归属,不管你知不知觉,承不承认。